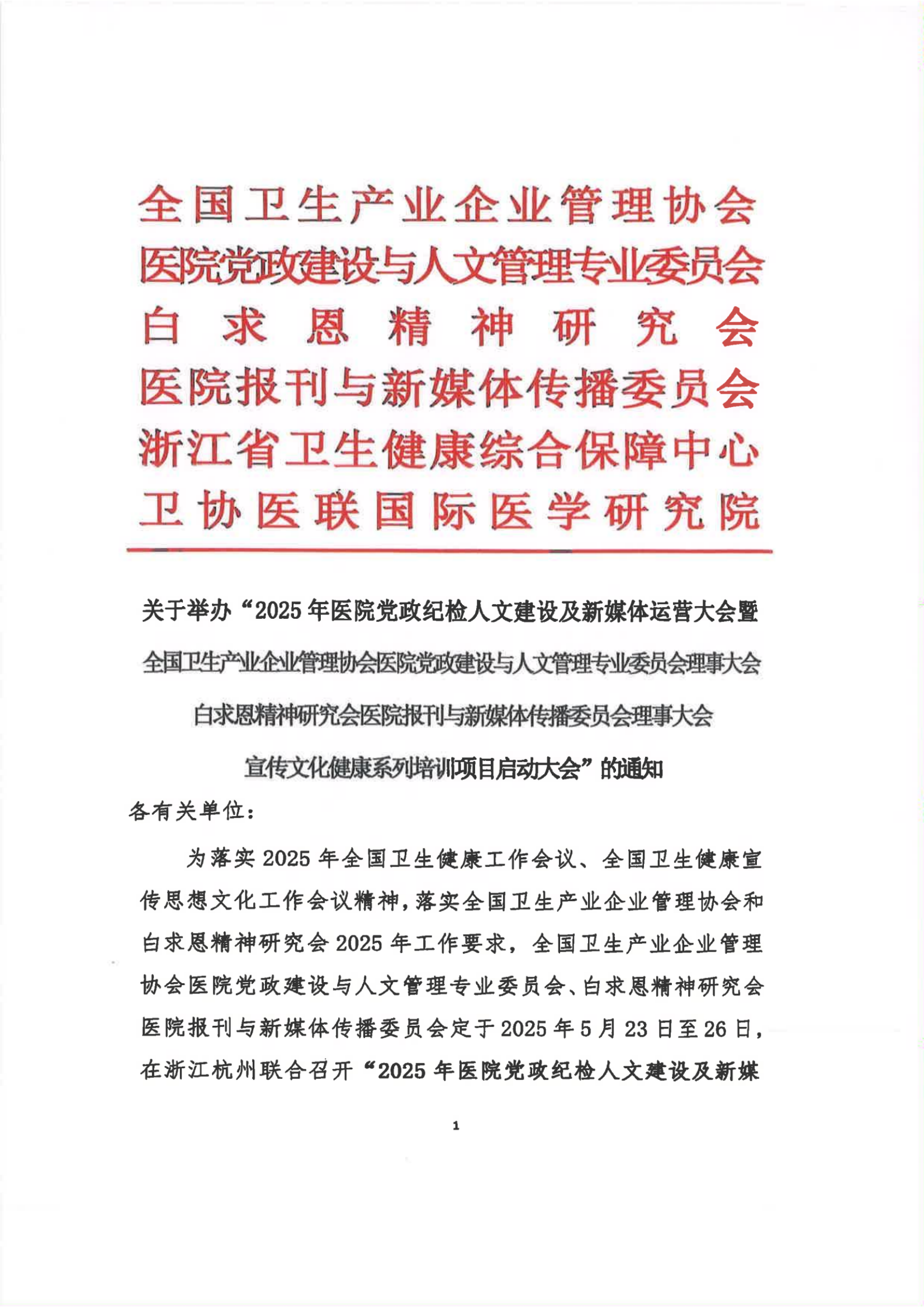1936年秋,诺尔曼•白求恩到达马德里。那时,背后有着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意大利支持的法西斯分子正进攻西班牙政府,引起了欧美进步人士的愤慨。成千上万的人离开本国,去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白求恩是其中之一。他到时,我已经在马德里一个月了,是加拿大委员会(向西班牙输送必要的医药供应的组织)驻这里的联络员。白求恩热情洋溢地对我说:“这 里是创造历史的地方!这里是我们要击退法西斯野兽的地方!”我们都是这样想的。当时的口号是:“决不让他们通过”,气氛如闪如电,令人激动,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兄弟般的庄严情感。白求恩到来前,我一直在前线采访,给加拿大的社会主义刊物写文章。他找我谈话,要我参加他的工作,当翻译。于是我们就出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以便他能为这个事业发挥最大作用。我们参观了许多医院和设在阿尔瓦塞特的国际纵队总部。这时,法西斯已经打到西班牙首都的郊区了,他们的宣传机器广播说,马德里已经在进行巷战,共和国政府随时会垮台。但是马德里不投降,一直顶到1939年春天战争结束时。这时,有一天,我们乘火车从阿尔瓦塞特到巴伦西亚。途中,他忽然对我说:“我有个主意,你听了说说你的想法。”然后他接着说,根据他从第一次大战得来的经验,如果前线或附近能有输血的条件,那么许多因流血过多致死的伤员是可以得救的。“你知道,亨宁,人血如果放在很低的温度下,能保存几个星期。我们现在要做的,无非是把西班牙所有能搞到手的冰箱都买来,组织献血小组,找医生和护士取血,再用汽车把血送到前方医院去。我知道过去没有人这样做过,可是如果得到西班牙政府的支持,我们是能够做到的。你以为如何?”他征求我的意见,使我受宠若惊,因为我是一点医药知识也没有的人啊。我说:“我看这样太好了。”就这样,我们去了巴伦西亚的“红色救济会”——一个相当于红十字会的共产党组织。接见我们的三个人都很年轻,只有二十来岁,但他们善于抓住形势、当机立断的本领却使我们深感惊奇。他们说:“如果你们能提供必要的器械,又能有加拿大的支援,我们就在马德里给你们一幢房子作为进行输血工作的总部;另外再派四个医生,还有护士、助理人员,统统归你们领导。”几分钟之内,事情就办妥了。于是白求恩和我便立刻去巴黎买医疗设备。在巴黎我们去了一家专售内外科器械的大商店。白求恩随便指着一种器械说:“那是白求恩肋骨剪——我设计的。”我不禁吃了一惊。可是他却不耐烦了。他说:“我打算去伦敦。那里我懂话,事情可以办得快些。”于是,我们来到伦敦买了设备和一辆旅行车。另一位加拿大人,黑曾•赛斯,也在那里参加了我们一伙。我们渡过英法海峡,把车子直驶马德里。他在成天炮轰和空袭之下,组织起了加拿大输血站。马德里的公民们都到这里来为受伤的男女儿童输血。这时的马德里,由于空袭和炮轰不断,有成千上万的人伤亡。
白求恩以他无限的精力,迅速而妥善地组织起了对马德里周围的前方医院和本城医院的血浆供应。此人是无所畏惧的。他常常冒生命危险工作。他总是念念不忘要到战场的最前方去。在瓜达拉哈拉战役中,我们给国际纵队的一名瑞典战士输了血。这是在瓜达拉哈拉城的医院里做的。我们输完血后,白求恩说:“咱们到打仗的地方去吧,看看那儿用得上我们不?”他指的是一个意大利师正向马德里进犯的地方,几天后西班牙政府在那里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我们出发,走上直通前线的大路。我们的车上带了一名西班牙医生和一名匈牙利摄影记者加扎•卡拉帕西。路上,白求恩对加扎说:“你还不忙起来!照点炮弹爆炸的好镜头嘛!”大炮在道路两旁不停地轰着。在我们就要接近我方部队时,一个意大利机关枪手发现了我们,向我们开火。白求恩在开车,便命令我们下车,隐蔽起来。我们照办,闪电似地扑在地上。子弹象鸟似的飞过来,离头几英寸。最后,意军枪手一定以为我们都死了。可是我们却没有受一点伤。回到车里,我们发现白求恩座位前边的挡风板上有一个子弹窟窿。这颗子弹是很可能穿过他的心脏的。他只差几秒钟的时间,幸免一死。如果死了,他的生命就达不到以后在中国的光荣境界了。
1937年2月法西斯拿下了马拉加城,当时白求恩正在西班牙南海岸的阿尔梅里亚城。十五万男女儿童步行逃出马拉加城,希望在距离二百公里以外的阿尔梅里亚找到安全的地方。他们沿途疲惫极了——饥饿,干渴,流血,还不断遭到法西斯飞机轰炸和机关枪扫射,再加上战舰的炮击。道路蜿蜒临海:一边是陡峭的内华达山脉,一边是大海。在这里遭到轰炸炮击,简直无处可逃。这样的大屠杀真令人心怖。白求恩忠于自己的原则,“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便开车奔驰在通向马拉加的公路上,去接运那些迎面而来的逃难人群。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是赛斯。然而对于后有法西斯追兵的逃难群众,想减少他们的痛苦是显然办不到的。于是白求恩决定用货车尽量把难民运到阿尔梅里亚去。他们俩在三天三夜中冒着法西斯的轰炸和炮火轮流开车,往返于阿尔梅里亚和难民之间。
白求恩似乎不知疲倦为何物。他对别人不耐烦,要求高,然而他首先对自己这样。当他要完成某项任务时,不管需要多长时间,他从不称倦。他以意志控制体力。然后,只要可能,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都能睡上一觉。我就见过他在铁路站台的沥青堆上纳头大睡。给白求恩当翻译可不是件容易事。他总爱把自己的想法直率地说出来。有一次他对我恼火了,因为他认为我给他翻译得不够有力。他要求高,对周围的人有时便不免粗鲁。但是他对伤员却象慈父般的体贴。在他那充满兴奋的活动中,他常常会一连好几天为他照料过的某个伤员发愁。我和白求恩初见时,对他完全不了解。有一次他和我一起通宵开车把血浆送到一处遥远的军事哨所去,他跟我谈到了他自己。他是一个成名的医生了,但除医疗之外,他的精力还用在许多方面——有社会工作,也有艺术。他曾度过一段愉快多趣的生活,但他对于所处的社会却越发不满了。他深刻感到,在这样拥有大量财富的社会里,却有人如此之贫困,真是不公道。他在1935年去莫斯科、列宁格勒出席国际生理学大会,他参观了苏联许多医院和诊疗所,印象颇深。回加拿大后,他便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他对我说:“我在那里找到了长期求之未得的答案。我辞去了医院里胸外科主任的职务,来到这里。我断了后路,再不回头了。我已经选定了道路。我是共产党员。”
白求恩所创建的输血工作进展得挺顺利。1937年夏,西班牙共和国军队接管了这项工作,白求恩便回到加拿大。他在全国到处旅行、演讲。然后,决定去中国为八路军服务。1938年初,他参加了毛泽东的部队,次年11月,在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战斗中献出了生命。
纵观白求恩的一生,似乎是为了他最后的一举进行着长期的准备工作——为了他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他早已在加拿大成名成家了,但他不以这些桂冠为满足。此人性急、热情,却有着对人类的深挚关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内心的愤怒也更强烈了——对社会的不公正和对资本主义世界统治阶级的虚伪所发出的愤怒;同时他对缺乏效率、拖拉作风和机会主义不能容忍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了。在他心目中有一种对未来世界的憧憬:人类都是弟兄,人剥削人的制度消灭了,自私和暴力遭到唾弃。他得出结论说,走向人类最后和最高目标的唯一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他要求他的生活能同他的信仰一致起来。他在中国之日,生活极度紧张,辛苦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但他终于感到,他果然达到了这种和谐合同的善境。
(本文作者原籍丹麦,精通多国语言。1936年11月白求恩大夫抵达马德里后,担任白求恩的翻译。白求恩大夫创建的西班牙加拿大输血站成立后,任联络官。现定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