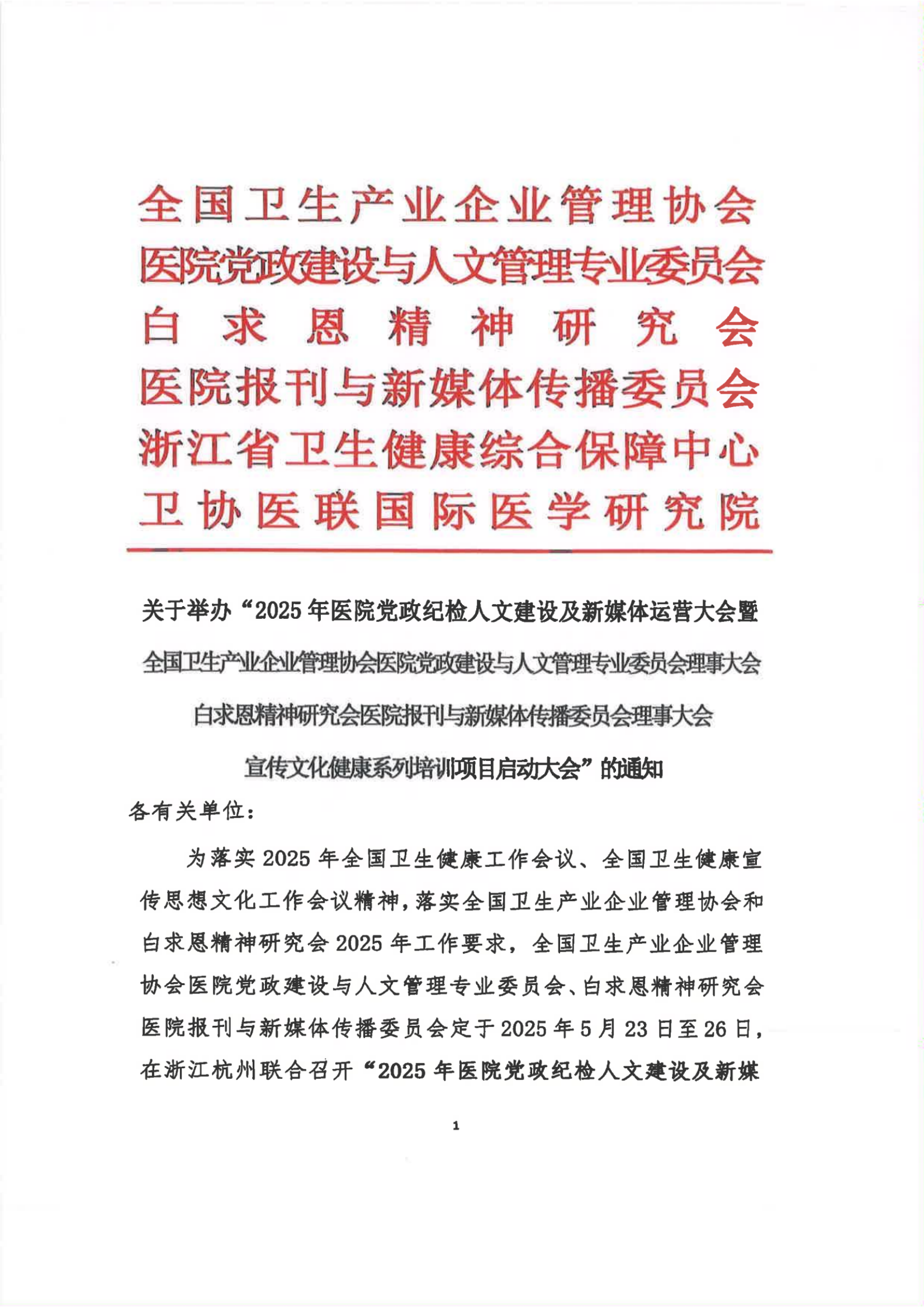当我敬爱的益友诺尔曼•白求恩逝世四十周年之际,我不禁回顾他的一生,探讨那影响他的发展和形成他的高尚品德的各种因素,追念他所走过的坎坷道路。我常爱把诺尔曼•白求恩的生平比作一株历劫偶存的树苗,在移植到了一个崭新的环境之后,终于长成为花果纷披的参天大树,简直就象一曲神话。相熟的人总是把这树看作“美丽的象征——永恒的喜悦”而长留胸臆。
读了以上的这段话,人们难免要问一问这树的萌芽过程如何,它扎根发育的土壤如何,它的风雨历程又如何。我执笔时深怀着近半世纪来人们对他的共同情感;我将谈到他发展的根由和环境,以及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他在性格方面经历了何等的变化。我还要附带提到以他的名字命名、以他的业绩为楷模的一所加拿大学府的情况。
二十年前,加拿大第一大城多伦多市以北几公里外兴起了一所全国规模最大的新型学府,约克大学。全校有全日制和半日制的学生各一万人。它象英国的某些大学那样采用学院制,各学院各有专业和特选的研究项目。校舍足以容纳数百以至上千名学生,包括寄宿生。1971年这所大学创办了它的第七所学院。这个学院何以命名呢?大家提出了十位候选人的名字,而绝大部分学生投票赞同以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来命名。白求恩学院对社会科学特别关心,着重于用社会科学来解决第三世界发展中的问题。1974年1月,学院新落成的大楼里举行了正式的命名典礼,这是在“中国周”里举办的为时三天的会议的活动之一。到场的有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参赞,亨宁•索伦森和已故的黑曾•赛斯;后两位于1936—1937年西班牙内战时期曾在白求恩大夫组织的输血站工作过。
这个学院除了举办专题讲座和讨论会之外,每隔一、二年都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会议来研究与白求恩有关的议题。在1979年4月5—7日举行的白求恩讨论会上,有十八位讲演人和一百多名教授和学生一起讨论了涉及医学政治学的种种问题。我的报告着重介绍白求恩和他对二、三十年代保健和医疗问题的见解,以及他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在准备讲稿的过程中,我又多次沉浸在往日我所亲历的那种激动、喜悦、振奋的心情之中。
近年来,每当我看到白求恩学院大墙上的“白求恩”这个名字时,看到加中友好协会举行白求恩电影放映会的海报时,特别是当我走过或驾车驶过耸立在蒙特利尔白求恩纪念场上的那尊美丽洁白的塑像时,我的内心不禁交织着骄傲、感激、赞叹,一种深情简直无法形诸笔墨。
诺尔曼在蒙特利尔工作了八年(1928—1936年)。我引以为荣的是,在此期间能够和他长年共事。第一阶段(1930—1932年),我们同在医院里看肺科病,主要是肺结核;以后我们在这方面还做过更多工作。在第二阶段(1935年12月到1936年9月),他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致力于改进我们的医疗制度,创建了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当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之际,医疗制度为人数众多的失业者和穷人所提供的治疗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魁北克省的情况更是如此。白求恩领导的一批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和一位牙医、一二位药剂师、一位统计学家,对当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他们还就各医院和诊所医务人员的配备问题,收取诊费和药费的问题,以及改进对病人的服务态度等问题,提出了四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分发给医生、牙医、护士协会和参加1936年8月省议会选举的近二百名候选人。然而,新上台的政府非常反动,因此并无下文。
我荣幸地参加过保健会的工作,并和我们的领导人白求恩一起工作到同年10月。当时佛朗哥的法西斯军队下决心要摧毁西班牙的民主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他出发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了。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在“白求恩社会医疗组”一直工作到1938年5月。我们还从事了一项活动,旨在研究五年来一直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二十五个家庭的营养问题,并且把蒙特利尔的贫、富之家和小康之家的男孩们的体重和身高作了比较。当时,十五岁的富家子弟的身材要比同岁的穷孩子高出十二厘米,体重偏重近四公斤。
我个人非常感激白求恩大夫的榜样对我的鼓舞;因为我比他年轻十岁,而我的性格和作风又和他迥然不同。我比较谨慎、保守,遇事时多顾虑、犹豫不决,易于陷入枝节问题。他急功激进,没有框框,无所畏惧,当机立断,不拘泥于琐事。泰德•阿兰和塞德奈•戈登在五十年代初合著的《手术刀就是武器》一书中,详尽地介绍了白求恩的生平,特别是他在中国的事迹。从那时候起,我在行动上也变得果断一些了,我时常喃喃自责:“麦克劳德啊,可别大惊小怪的;象白求恩那样干起来吧!”
缅怀白求恩时使我心情激动的第三个原因是,我对他钦佩和仰慕特甚。他的朋辈都知道,他有时要闹点小脾气。他是一个生气勃勃、富有进取心和自发的创新精神的人,经常有新颖的见解,但在意图、愿望和行动之间有时产生矛盾,有时态度不免失之粗鲁;这一点我在下文中还要谈到。他三十六岁那一年得了肺结核,却又出奇地活了过来。他逐步通过新的生活体验,“迅速而又真诚地对每一项造福于人类的新的真知灼见和对社会上的各项难题,都作出自己的反应”。对此,我不能不深为赞佩。这还使我更深入地观察了他的个性、脾气、举止。从1935年底直到他逝世时为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表现了“自相矛盾的个性的统一”。
这种惊人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白求恩从此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并且都处置得当。尽管如此,中国人民对他是有深刻认识的;他的主要精神表现为对他人的体贴关怀,富于同情,毫不利己,热情地献身于他一生中最伟大、最崇高、最有意义的事业。
他还有许多值得钦佩的才华。他青年时有过特殊的经历,森林伐木工人的生涯使他经受了磨练。这些经历伴随他逐步地成长为外科医生,而恰好又为他日后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担任的职责作了充分的准备。
最后,正当白求恩有资格就任一项会使他扬名于世的要职的时候,中国的战局恶化了。他毅然走上了展现在他所选定的生活大道上的另一段历程。这种历史的巧合使我赞叹不已。在西班牙工作之后,如果他再愿意从事胸腔外科,我确知至少有两位身居要职的美国外科医生愿意推荐他出任优越的职位。但是他拒绝了;在中国人民最需要他运用他卓绝的才智来为他们服务的时刻,他选择了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道路。中国人民在延安精神的指引下,于抗击侵略者的同时开始重新建设社会。也正是在延安精神的照耀下,这朵加拿大的奇葩遂得以勃然而作。
青年白求恩是在怎样的生活环境中生长、成熟的呢?他早期生活的背景有助于他成长为一个多才多艺,不无粗犷却是十分朴质,充满创新精神和勃勃信心,对人类极富同情的人。他颇异于北美今日的许多后生;他具有明确的生活目标,有一整套的道德观念,准备献身于艰苦工作而义无反顾。他不受“人皆为己”的私欲所支配;他摆脱了那种曲解个性自由,对家庭、邻人、社会一概都不想尽义务的浅陋哲学的影响。诺尔曼自幼就确立了日后的志向,他要象他的祖父(也叫诺尔曼•白求恩)那样,当外科医生;也许还同样地象他那样当个艺术家。
白求恩的父母为家里三个孩子树立了高尚的道德标准。他们虔诚地信奉宗教的哲理,其中包括《圣经•新约》中的戒渝:“象爱护你自己那样地对待他人。”他们恪守的另一信条是:如果路遇长者或有难者请你扶他走一里路,你就应该扶他走二里!白求恩家的孩子们经常对贫病孤苦之家有所馈赠。多年以后,诺尔曼曾在大雪之夜把自己的大衣披在一个在风寒中战栗的穷人身上,这是不足为奇的。1931年我在维多利亚皇家医院协助他工作时,有一次我们要病人回门诊所去,以便观察他们对一种新治疗法的反应。这时,白求恩知道病人中有几个苦于负担长途跋涉的火车费、汽车费,便出钱资助他们。他对他们的困难如此关切,这也是不足为奇的。贯穿着他一生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显然是承袭了他双亲舍己为人的传统。
在通常情况下,他总是对人体贴入微、慷慨大方,易于相处;特别在孩子们身上,他无不倾注满腔的热忱慈爱。这些性格的形成,可能与他幼年时期在安大略省北部边境的拓荒小城里渡过的生活有关。在当地的印第安人中,那些体格健壮和行动敏捷的伐木工人和水手给他的童年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在醉后争吵时,往往要“饱人以老拳”,但是他们的心地是热情的。白求恩十七岁上中学的那一年,从10月起到次年4月,在边远的一个伐木工人营地整整当了一冬的伐木工人,另一年也如此。他经常在晚上为没有受过教育或只受过很少教育的本地工人和移民工人办夜校。暑假,他又去轮船上当水手。除了这段在野外做工的经历外,他还当过小贩和担架兵,后来,二十五岁那年,在法国伊普雷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负伤而退役。生活经历使得他在遭受压力和失望时,常在言谈举止中有近似的表现,于是就不免引起加拿大城里中上阶层的守陈拘礼之辈的反感了。
另一方面,白求恩时或也表现出与上述作风形成鲜明对照,颇如英国士绅那样的风度闲雅,涵养凝重。他写过一些好诗;他画的一幅画曾在蒙特利尔美术馆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新作展览会上展出。有一两次,他以外科顾问的身份到维多利亚皇家医院的病房检查需作外科手术的肺结核患者时,竟给人留下了一种典型的英国军官的形象。原因何在?只因他步履矫健,体姿端正,又蓄得一撮军式小髭,望之威严。可是,一个有时象假日狂欢的水手,有时又吼着向手下人发命令的人,怎么可能出现这种风度呢?我想它可能反映了他复杂的人生经历的另一个方面吧。
诺尔曼的母亲原籍英国,嫁到白求恩家带来了优雅的传统。她曾经几次带着三个孩子回“故国”去探亲访友。虽然泰德•阿兰和塞德奈•戈登(《手术刀就是武器》的两位作者)或罗德里克•斯图尔特(白求恩传记的作者)都没有提出可供研究的资料,来说明青年白求恩受到了多少“舒适、优雅的生活”的薰陶。然而可以肯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他在英国皇家海军当军医的那些日子,以及战后他在伦敦和爱丁堡进修时期,他经常接触到美术馆和芭蕾舞,并且深深地为古老的文明和相应的社交生活所吸引。他正是在这种社交圈子里认识弗朗西丝然后结了婚的。在她身上可能体现了这个北美伐木工人所渴求的那种雍容华贵的气质;而她可能从来没有以同情的态度去理解白求恩性格中的其他重要成分,更没有料到他们的共同生活竟会陷入矛盾重重,终于水火不容的地步。
追溯往事,我们可以认为,白求恩一生中几起明显地带有悲剧色彩的遭遇,实际上有助于他之达到伟大的境界。他长期憧憬的外科医生的名誉地位,恰巧在他肺疾发作和婚变突起之际归于幻灭。两年来在底特律取得的外科临床方面的许多成就看来只不过是春梦一场。他作好了迎接新考验的准备。他在疗养院接受治疗期间,一当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恢复健康的时候,就下决心要掌握胸腔外科的新技术来拯救肺结核患者的生命。根据他在蒙特利尔的长年经验,他发现人民的贫困加上医疗制度上的失当,竟使他的外科术无用武之地——它对肺结核患者收效甚微,也往往为时过晚。从此他转向研究引起经济危机和贫困的社会痼疾。这期间,他访问了苏联;进行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良心上的自我反省”,并终于加入加拿大共产党,使他那种不甚协调的个性在内心深处一体化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许多爱好,只不过是按其轻重缓急重新加以调整而已,其结果,上文已经谈到。
或问:如果白求恩活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又将如何呢?老友中有人担心他是否能安于和平时期协作生活的节奏。但是那些在1936年在蒙特利尔保健会与他共事的人,那些目睹他献身于西班牙内战的人,对这样一位目标明确的人的精神和作风都是十分钦佩的。白求恩从巴甫洛夫的生物条件反映论中得出结论: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面貌是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行动来加以改造的。他在中国的贡献和所受到的爱戴使我确信,如果今天他还活在世上,他准会同另一位伟大的外国医生马海德一起,在毛主席、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将军和其他中国同志的领导下,欣欣然孜孜然致力于中国的建设事业的。
(本文作者三十年代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和白求恩大夫共事多年,参加过白求恩大夫发起的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的活动,是《白求恩在蒙特利尔》一书的作者之一。)